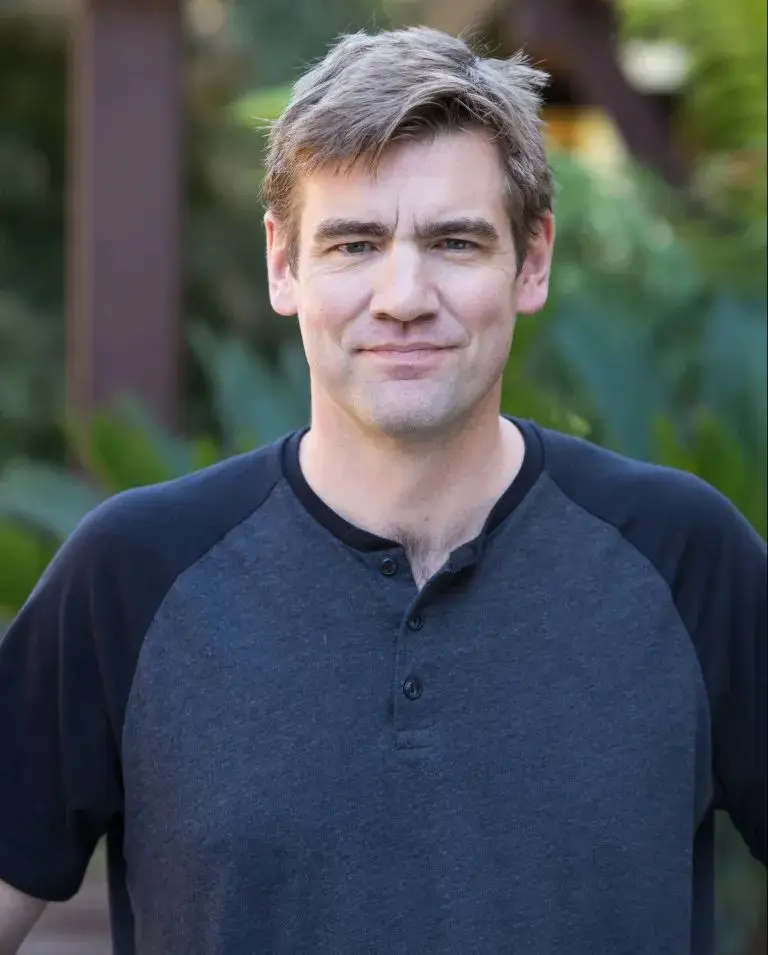
Chris犀利指出当今互联网已被巨头垄断,创新活力遭受严重扼杀。他认为区块链作为新兴计算平台恰逢其时地出现,如同一面在硅谷重新升起的海盗旗,引领人们投身于充满趣味性、略带冒险精神且极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浪潮。MarsBit编辑特别推荐读者细读本文,深入了解这位顶尖风投合伙人看好区块链与加密货币背后的深层逻辑。
Q:您在访谈中提到外界存在一些不安全因素,这是否是您倾向于保持个人隐私的主要原因?
Chris Dixon:确实存在不少极端行为。甚至有人直接闯入我家,误以为那里存放着比特币。
Q:从哲学研究转向科技投资的职业轨迹中,哪些核心认知对您的工作产生了持续影响?
Chris Dixon:最初是AI与计算机科学的碰撞将我引向哲学道路,尤其是《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这本书对我影响深远。高中时我写过一篇探讨机器能否思考的论文,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这段经历让我对历史与创新的关系产生持久兴趣——技术变革往往源于人类对根本性问题的追问,而非功利性目标。这种认知至今仍影响着我的投资逻辑:真正颠覆性的创新,常诞生于对"问题本身是否有趣"的纯粹探索中。
Q:您提出的"问题的有意思程度"驱动创新理论,能否具体阐释这种非功利性探索对技术突破的实际作用机制?
Chris Dixon:回顾历史上的重大创新,往往都是由一小群痴迷于某个问题的人推动的。驱动他们的不是实用性考量,而是纯粹觉得这个问题"有意思"(interestingness)。比如比特币借鉴的许多早期技术,那些研究者根本没想过要挑战美联储或颠覆科技巨头,他们只是单纯被那些晦涩的专业问题所吸引。
我在一篇广受欢迎的博文中曾写道:"现在最聪明的人周末做的事,会是其他人未来十年的工作。"技术史上那些在车库和宿舍里诞生的突破并非偶然,而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很少能提供让人长期专注的环境。虽然也有专家学者和政府资助的项目,但大多数有才华的人都在企业工作,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基于兴趣做出的探索,往往最具前瞻性——即便当时看起来毫无实用价值。
Q:如何评价中本聪比特币白皮书的"低调开端"对后续区块链技术发展产生的深层影响?
Chris Dixon:中本聪的比特币白皮书完全没有宣称要颠覆世界。我把这份白皮书贴在墙上——它出奇地简短,一张海报就能容纳全部内容,这种低调的开端耐人寻味。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潜水艇策略":刻意将革命性技术包装成不起眼的小发明;也有人觉得这种轻描淡写的技术讨论背后暗藏深意,用极简的数学语言掩盖了可能引发的范式革命。这种矛盾性恰恰成为区块链运动的隐喻:始于技术极客的晦涩论文,最终却重构了全球价值传输的基础协议。
Q:比特币区块大小之争反映出哪两种根本性的技术理念冲突?您为何认为以太坊的出现标志着区块链技术的范式转移?
Chris Dixon:比特币区块大小之争表面上是关于GitHub代码中一个参数的调整,实则折射出区块链技术底层两种根本理念的对立。一方是密码朋克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将比特币视为颠覆传统金融体系的工具;另一方则像我这样,将其看作可构建多元应用的底层架构。我们不仅主张扩大区块容量,更希望为其添加的编程语言功能,以拓展其可能性——虽然这个阵营最终落败。
2014年以太坊的诞生实现了我们未能达成的愿景。它本质上延续了我们的技术理念,通过图灵完备的智能合约系统,将区块链从单一的价值存储媒介升级为可编程的计算平台。这种突破标志着区块链技术从"数字黄金"的单一叙事,转向了支持去中心化应用的通用基础设施,完成了真正的范式转移。
Q:从互联网发展史视角看,中心化平台垄断导致的"公共-私人关系失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种失衡将对创新生态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
Chris Dixon:互联网最初是以开放、去中心化的协议为基础建立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8年左右。智能手机的普及成为一个转折点,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这些中心化服务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早期的互联网时代,像Mark Zuckerberg或Larry Page这样的创业者可以自由地创建网站,不必担心大公司会突然要求分走30%的收益或改变规则——这在去中心化的架构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可以用城市街道来比喻:街道是公共的,而路边的餐馆是私有的。餐馆的生意依赖于公共街道带来的客流,这种公私关系原本是平衡的。但现在的互联网更像是迪士尼乐园——如果你在乐园里开餐厅,乐园随时可以抬高租金或改变规则。脸书、谷歌和苹果构建的生态系统就是如此,它们单方面掌控着规则制定权。
这种失衡正在扼杀创新。互联网变得不再像从前那样多样化、令人激动和富有创造力。许多有创意的商业模式因此夭折。如果我们不改变现状,创业领域将付出巨大代价,下一个Zuckerberg或Page可能永远无法起步。
公私领域都需要存在,不是所有东西都应该公有化——那会变成另一种计划经济。有两种恢复平衡的途径:政策调控或市场创新。我更倾向于后者,通过自由市场竞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Q:区块链技术如何通过"代码治理"实现对Web 2.0时代"不作恶"原则的范式升级?这种转变将如何重构数字时代的权力分配机制?
Chris Dixon:区块链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提供更丰富、更先进的协议体系。它继承了Web 1.0最宝贵的去中心化治理特性——规则被固定编码在协议中,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自由创造和投资,同时又具备更的技术性能。
我们可以把区块链看作一个由社区共同拥有的数据库。Web 1.0时代缺乏真正的状态记录能力,而现在的以太坊等区块链平台可以存储任何代码、名称或其他数据。这种丰富的数据库为构建更的服务提供了基础,同时保留了Web 1.0和Web 2.0的优良特性,这也让很多人将其称为Web 3.0。
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范式转变:Web 2.0时代的理念是"不作恶"(Don't be evil),而Web 3.0则通过代码实现了"不能作恶"(Can't be evil)。这种转变将治理规则直接编码在协议层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数字权力的分配机制。
Q:您将区块链比作"硅谷再次升起的海盗旗",这种颠覆性创新的扩散过程面临哪些结构性障碍?如何突破这些限制实现主流化?
Chris Dixon:区块链确实像一面重新在硅谷升起的海盗旗,它象征着一种充满冒险精神、略带危险性却又极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浪潮。要实现主流化,主要面临三个结构性障碍:首先是技术复杂性带来的认知门槛,普通用户难以理解其底层逻辑;其次是现有监管框架与去中心化特性的天然冲突,这需要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合规路径;最后是基础设施的完善度,包括交易速度、能耗效率等工程挑战。突破这些限制需要技术社区保持开放协作,通过开发者工具简化应用构建难度,同时与监管机构展开建设性对话,在关键性能指标上持续迭代优化。
Q:面对互联网发展周期中"创新-垄断-僵化"的历史循环,区块链技术能否真正打破这一宿命?其去中心化特性在哪些层面具有突破性价值?
Chris Dixon:我们总要尝试打破这个循环。传统互联网协议的演进模式通常是由标准研究机构或基金会制定规范,再由多方实现具体应用,比如IRTF制定网页协议后,Chrome、Firefox等浏览器基于此开发。以太坊也遵循这一路径,这是最成熟的协议运作方式。
比特币则是个特例,它没有独立的协议文档,代码即协议,且主要由核心开发团队控制。这种模式确实可能重蹈中心化覆辙,但区块链至少为我们争取了10-20年的变革窗口期。去中心化的突破性在于将权力从单一实体分散到整个网络,通过共识机制和开源特性确保规则透明,这种架构本身就能抑制垄断的形成。就像以太坊展现的,当协议层保持开放时,开发者能在其上自由创新,而不会受制于平台方的任意规则变更。
Q:以太坊的Token经济模型如何通过利益绑定机制解决传统互联网平台与内容创作者之间的价值分配矛盾?请结合具体应用场景说明其运行逻辑。
Chris Dixon:以太坊展现了一种革命性的商业模式。与传统互联网平台依赖广告收入不同,它通过发行token来激励社区发展。这种设计最精妙之处在于:当网络扩张时,token价值随之增长,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
历史上所有网络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平台与生态的内耗问题,比如Facebook与新闻出版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Token经济模型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矛盾——通过让贡献者和用户持有网络token,使个人利益与网络发展直接绑定。
以Twitter为例,如果采用区块链协议构建一个通用的微信息平台,让所有用户都持有一定数量的token。那么随着平台价值提升,每个参与建设的人都能获得token增值的回报。这种机制天然形成了正向激励:用户越积极参与内容创作和社区建设,平台发展越好,个人收益也越高。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平台"吸血"内容创作者的零和博弈关系。
Q:从瑞波投资到设立专项加密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的战略转型反映了区块链领域哪些关键性趋势变化?
Chris Dixon:2013年我们首次投资Coinbase时,区块链领域仍被视为密码朋克运动的延伸。但以太坊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认知——它让技术人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可构建应用的开放平台,而非仅仅是意识形态工具。这种转变直接推动了人才的大规模涌入。
我们设立加密基金的逻辑很明确:与其投资传统股权结构的企业,不如直接通过持有token参与新型商业模式。这种模式跳过了中间商环节,让资本与技术创新的结合更紧密。本质上,我们是在跟随技术人才的脚步——当他们开始用token构建去中心化网络时,我们的投资方式也必须同步进化。
Q:区块链技术如何重构传统风险投资的法律定义与运作模式?这种重构对数字资产投资的合规性提出哪些特殊要求?
Chris Dixon:从本质上说,加密货币投资与传统风投有相似之处——我们都为技术人才提供资金支持创新。但法律定义上存在关键差异: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当我们通过专项基金直接购买Token时,就不再符合传统风投基金的法律定义了。
具体到加密货币基金这个小范畴,我们不得不注册为对冲基金架构。这带来一系列特殊合规要求,比如必须遵守SEC关于禁止使用加密通信等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悖论是:恰恰在这种架构下,我们反而获得了直接持有Token的合规操作空间。这种法律身份与业务实质的错位,正是区块链重构传统金融规则的鲜活例证。
Q:作为区块链投资的重要参与者,您如何看待加密货币领域"技术理想主义"与"投机泡沫"的共生现象?这种矛盾对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哪些潜在风险?
Chris Dixon:这个领域的大多数从业者都是技术背景出身,他们本质上希望合规运作,但面对新兴行业尚未明确的监管框架时,难免会遇到困惑。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们寻求专业法律顾问的帮助,也主动提供合规支持。不过必须承认,加密货币作为新兴领域,许多监管边界仍处于探索阶段,这种模糊性确实会给行业带来不确定性。
Q:您预测区块链计算平台将催生哪些颠覆性应用场景?这些应用如何突破现有互联网服务的边界?
Chris Dixon:区块链本质上是一种新型计算机,自然会催生与之特性匹配的创新应用。如果有人宣称要在区块链上复刻《堡垒之夜》这类传统游戏,我会质疑这种思路是否合理——这很可能既无法发挥区块链的优势,又受限于其性能瓶颈。
应用层最活跃的领域集中在金融和游戏方向。比如非同质化代币(NFT)重构了虚拟物品的权属逻辑,而现实资产上链则开辟了价值流转的新范式。至于用加密货币买咖啡?这可能是最缺乏想象力的应用了——支付问题早已被解决。更具突破性的是为全球10-20亿缺乏银行账户但拥有智能手机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真正的颠覆性机会在于那些传统互联网无法实现的服务:基于智能合约的自动化金融协议、玩家真正拥有游戏资产的虚拟经济体,以及通过分布式存储协议重构的云服务生态。这些创新不是对现有服务的简单迁移,而是通过区块链不可篡改、去中介化的特性,重新定义数字世界的协作规则和价值分配机制。
